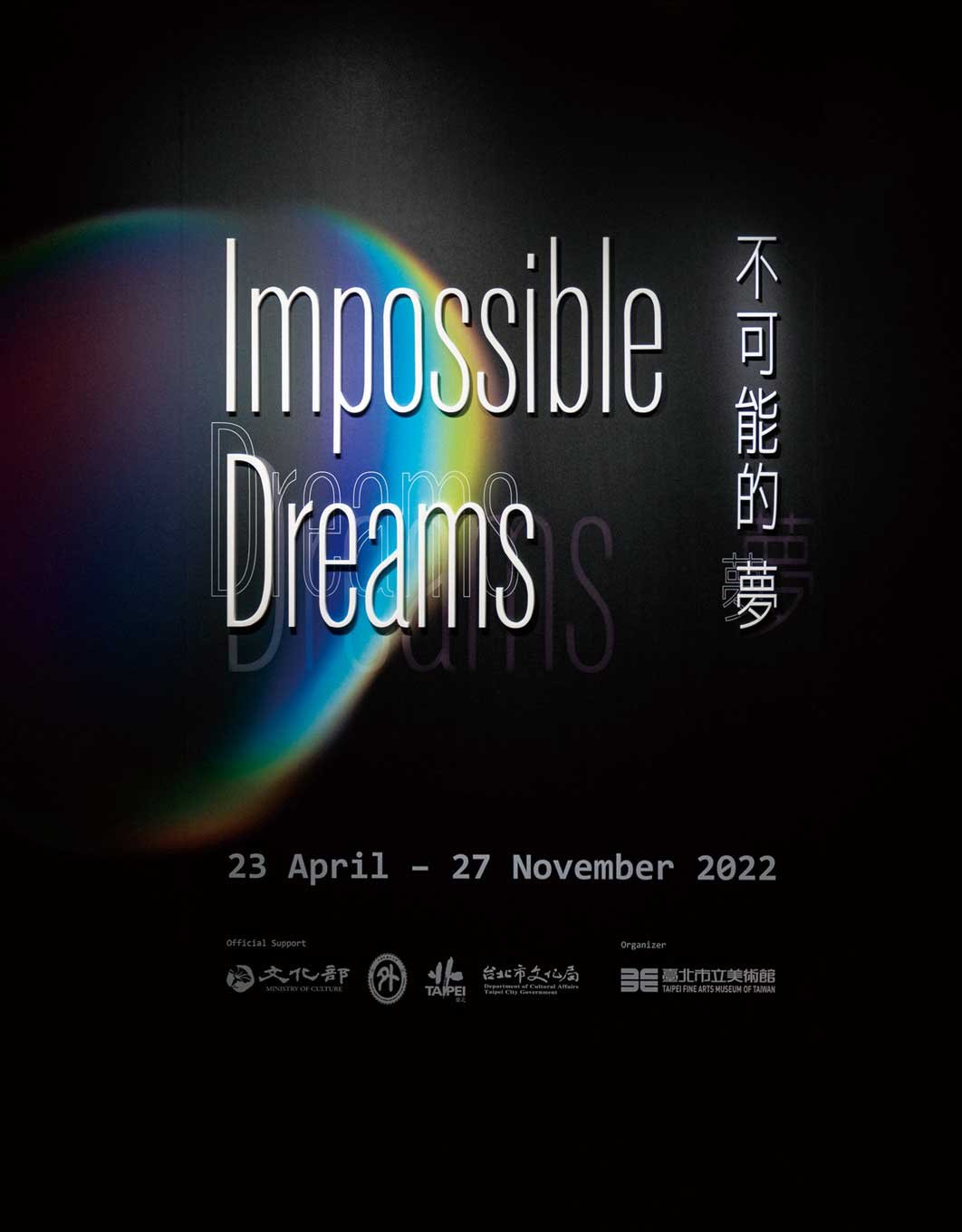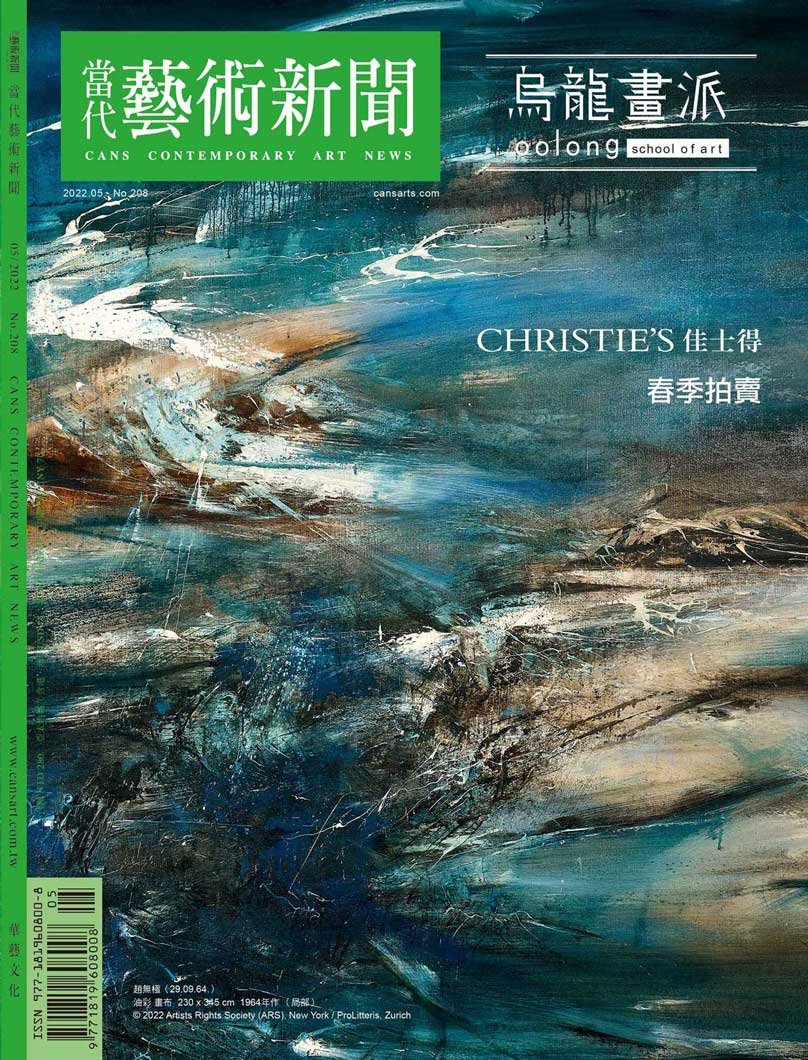回首來時路 台灣館【不可能的夢】展現逆勢中的生機
余小蕙/威尼斯報導
圖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因疫情延宕了一年的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終於在4月20-22日順利舉行三天專業預展,並於23日正式向公眾開放,就此拉開長達7個月的展出(展期至11月27日)。設在威尼斯總督宮旁普里奇歐尼宮的台灣館,照例再度出席這場全球藝術盛會。然因原代表藝術家撒古流涉性侵事件,北美館於今年年初臨時取消原展覽方案,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緊急籌措了一檔名為【不可能的夢】的展覽,通過邀請函、現場照片、影片、主視覺、媒體資料、畫冊等史料,以及七件曾參加展出的作品作為「活檔案」,建構一個關於台灣1995-2019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歷程的記憶空間,通過梳理呈現台灣館至今13屆的發展與蛻變,既是回顧,更在展望未來。

。.jpg)
文獻展看似簡單,卻往往是最棘手和複雜的。文獻的保留,在避免歷史被遺忘,被簡單化,片面化。然而,在一個經常只能「走馬看花」的威尼斯雙年展,更何況對台灣國際政治、藝壇等情況完全陌生或不見得感興趣的觀眾,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和觀展時間內,呈現這段艱難複雜的參展史,可謂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就以位於動線一開始那張邀請函為例,一紙1995年5月11日,當時威尼斯雙年展大會主席郎迪(Gian Luigi Rondi)寄給北美館當時代理館長蔡靜芬的邀請函,寫著「…高興正式邀請台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慶祝一百週年的』此次盛會…」,雖是簡單而制式化的措辭,但這紙得來不易的傳真,背後卻代表了台灣機構多少的努力,以及台灣藝壇的種種的夢想和期待!這些,造訪普里奇歐尼宮的觀眾,絕大多數並不知情,展覽也未必能讓他們了解;對觀眾來說,這是台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開始,僅此而已。
正如近30年台灣館展出從多位藝術家聯展到個展的演變,北美館知道,在威尼斯雙年展這樣一個獨特的國際平台上,儘管所有國家皆以「國家」的名義,但「藝術」才是交流和對話的唯一語言;過多的強調台灣,對推展台灣藝術家並無助益。因此,此次台灣館文獻展選擇了梗概的敘事策略,每一屆台灣館,一面牆,標註著展覽名稱,策展人、參展藝術家的名字,展覽介紹;一個展覽櫃,呈現該屆現場展出的各種形式的證據。

然而,也正如絕大多數觀眾並不知情此次文獻展背後的緣由和匆促,多少又給了人以「台灣」為說事的感覺。雖是一項簡潔有效、內容也算多彩的「簡報」展,但台灣館獨特的政治糾葛,每一屆展出所經歷的國際外交上的斡旋,台灣藝壇的辯論和爭議都被省略掉了,也失去了文獻展本該富有的龐大潛能,亦即揭露和召喚那隱藏在表面底下曲折複雜的血肉筋脈,以及靈魂。就連展覽的一大亮點——除了文獻,並且展出了曾在台灣館展出,皆與身體和行為相關,並多少隱喻呼應了本屆雙年展【夢之乳】主題的7件作品,包括姚瑞中的〈本土佔領行動〉的金馬桶和照片;崔廣宇的行為錄像〈十八銅人,表皮生活圈,城市精神〉;湯皇珍〈我去旅行V〉;蔡明亮〈是夢〉;陳界仁〈帝國邊界〉;張乾琦〈中國城〉;謝德慶〈跳〉——也以「活檔案」的姿態呈現,犧牲了藝術品的主體性和空間感。
然而,對於知道此次台灣館臨陣換展的人來說,不該過多苛責這次文獻展的欠缺和不足,反而應該肯定北美館的堅持和努力——得來不易的參展機會和場地,怎能輕易中輟!無妨將此次文獻展視為一次「歇腳」和「過渡」,是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之際,重新思考下一屆參展內容和策略的契機。因此,由原策展人派崔克.佛洛雷斯(Patrick D. Flores)擔任總召集人,訂於7-10月舉行,透過線上傳播的四場「國際論壇」,被賦予了重大期望。來自台灣、菲律賓、科索沃、西班牙、德國、印尼、南非、捷克的主講人,對當前國際關注的一些議題「為什麼構成了國家館?國家館又產生什麼?」「時間、身體、科技」「歷史生態學」「他人的自由/他種自由」所進行的討論,或能為為台灣館再出發提供思想和精神動力。


專訪/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王俊傑
【不可能的夢】是一種期望 也是一種理想的展現
余小蕙(Yu Hsiao Hwei)/威尼斯專訪
余小蕙:這次展覽著重在威尼斯台灣館現場檔案的呈現,其他如前期準備和作品構思和製作等文獻一概闕如,首先請說明一下本次文獻以及展出作品的篩選標準。
王俊傑:因為撒古流事件,北美館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決定了文獻展的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也思考到展場空間的侷限,如何呈現十三屆、近30年的文獻——尤其在一個觀眾不見得對我們的歷史有興趣的威尼斯雙年展?因此必須是一個簡潔的概覽,而且不能只有檔案,仍需要有一小部分的作品。當我們重新檢視每一屆參展藝術家作品時,發現很多作品具有與身體、行為相關的特性,因此選了7件透過身體去表現包括對政治等議題討論的作品。因為是把作品跟13屆檔案混合起來的展覽形式,就難以將當年作品如何產生以及背後中中討論等延伸概念鉅細靡遺的展現。我們希望讓觀眾很快體會到台灣館13屆以來的歷史和演變,從一開始每屆很多藝術家逐漸變成單一藝術家,主題也從一開始非常強調台灣,到後來慢慢讓藝術品自己說話、和觀眾溝通的歷程。我們從現有的檔案庫裡搜尋、討論和篩選,決定每屆必有的共同元素(如主視覺、題目、藝術家、媒體文宣或畫冊等等),以及配合歷屆藝術家不太一樣的檔案,例如,上一屆鄭淑麗當時拍片的囚服。

余小蕙:以【不可能的夢】作為台灣館近30年歷史的註腳,給人一種頗悲情、挫折的感覺……
王俊傑:【不可能的夢】有著雙關的寓意,一開始可能帶有幻想,但正因為不可能,所以希望它成為可能。我們處理台灣身份這個議題時,經常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拉扯:在威尼斯雙年展這樣一個國際平台時,我們該如何去面對國際藝壇,跟其他人平行對話;而台灣的政治現實卻受限於其曖昧的國家地位,很多事情無法一蹴而就。這時,藝術的專業呈現變得更加重要。當你的藝術能量夠大時,你才可能受人尊敬,這是國際藝壇的常規。【不可能的夢】是一個「期望」,至於是否真能成真,就像我們常說的,藝術家永遠是提出問題,但不能解決問題,藝術家往往懷抱著理想性一樣,【不可能的夢】也是一種理想的展現。

余小蕙:七月登場的「國際論壇」,起作用在於為下一屆台灣提出願景?
王俊傑:這次的撒古流事件打亂了我們原先的單一、且是原民藝術家的方案,本來可以名正言順地和這次關於女性藝術和原民藝術這個國際潮流議題發生對話,現在只能透過論壇,針對我們觀察到的國際現象,包括藝術、國家館的意義;自由、身體、科技等呼應全球化、後全球化的議題進行討論,藉以思考台灣館下一屆的展覽。但我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威尼斯雙年展在全球藝壇裡面是一個非常講求策略的平台,它與我們一般說的所謂的藝術內涵、深刻性,不太一樣。它是一個百家爭鳴,非常競爭的場域;背後是策略、行銷、政治意涵等因素在運作,這和單純策劃一項展覽不太一樣。

余小蕙:那麼「國際論壇」的討論更多是針對台灣藝術界,還是希望藉此串連台灣和非西方主流國家藝術界的合作?
王俊傑:基本上我們目前所做一切都是同時面對這兩個部分,一是台灣自己,另一就是國際。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操作。台灣畢竟是自成一個體系,關注的面向和國際上討論的議題不盡相同,這對於想要走國際路線的機構或個體來說,都是相當麻煩的,即一件事情要做兩套,因為台灣礙於其現實狀況,不得不去面對台灣的輿論、政治、其整體發展脈絡。我們必須同時面對這兩個核心,而不是偏向哪一個部分。我們這次繼續借重策展人佛洛雷斯的國際人脈和對事物敏銳的洞察力,挑選的講者,除了台灣,大部分都是非第一世界、非白人的,在拉美和跨領域的實踐者,期待拓展和不同平台的對話和串連。

台灣館【不可能的夢】,威尼斯普里奇歐尼宮,2022年4月23日–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