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wamoto Fumiwo(日本國立藝術研究中心策展人、譯者與專案統籌)
我初次接觸糖果鳥的作品是在2019年,當時他正參與福岡亞洲美術館的駐村計畫。那時,他正在進行〈他者〉(The Others)系列計畫,透過在不同地方捕捉「局外人」——如移民等群體的故事。他邀請這些人書寫他們的故事,再將其轉化為繪畫和塗鴉的創作素材——換言之,他將這些故事轉譯為視覺藝術,以傳達給更廣大的觀眾。在福岡版本的《他者》中,糖果鳥與一位在當地韓國學校任教的女性藝術教師合作。聆聽她作為在日韓國人(Zainichi)社群中成長的個人故事,以及其脆弱而複雜的身份認同,糖果鳥創作了一系列繪畫作品和幾件臨時性的塗鴉作品。儘管《他者》系列中合作者們的故事往往觸及更廣泛的社會議題,例如移工遭受的不當對待和根植於社會中的歧視制度,但糖果鳥的作品更著重於這些人如何用自己的語言描述處境,而非採用對他們而言陌生的語言或表達方式。〈他者〉是藝術家嘗試基於這些尋找自己在社會立足之地的局外人所寫的文字來創作,這種「不屬於某處」的感受也是藝術家本人所體會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計畫或許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透過不同個體的經驗來重新審視自己對社會歸屬感的不適與不確定性。
_壓克力、畫布_65×50×2cm-e1731642847368.jpg)
(十五)
壓克力、畫布
65×50×2cm
_壓克力、畫布_53×33cm.jpg)
(十一)
壓克力、畫布
53×33cm
_2024_複合媒材、畫布_65x53cm.jpg)
(七)
2024
複合媒材、畫布
65x53cm
在福岡協助他的計畫期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陳列在作品旁的速寫本。這本子保存了創作過程中的粗略素描、文字片段和一些Found Objects(現成物)。雖然我無法完全理解其中的中文文字,但我感受到這速寫本是糖果鳥創作中的重要元素。與描繪他人故事的作品不同,速寫本蘊含著藝術家尋求充分表達的個人聲音。我可能會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我有機會在其他場合閱讀過糖果鳥所寫的一些文字。他的文字雖然捕捉日常生活的場景,卻似乎巧妙地避開描寫文中人物周遭的更大處境。透過描述父母與子女間緊張的關係,或是穿著黑色T恤的人們,城市的氛圍隱約滲透出來。然而,文字從未直接或具體地描繪外在世界。相反地,通過保持專注於約五公尺範圍內發生的事物的個人視角,以及記錄著越來越向內的自我對話,糖果鳥的文字最終找到了與讀者內在聲音重疊的交集,有時還會觸發意想不到的回憶。

〈河畔煙火〉作品截圖
彩色4K錄像作品
11mins10se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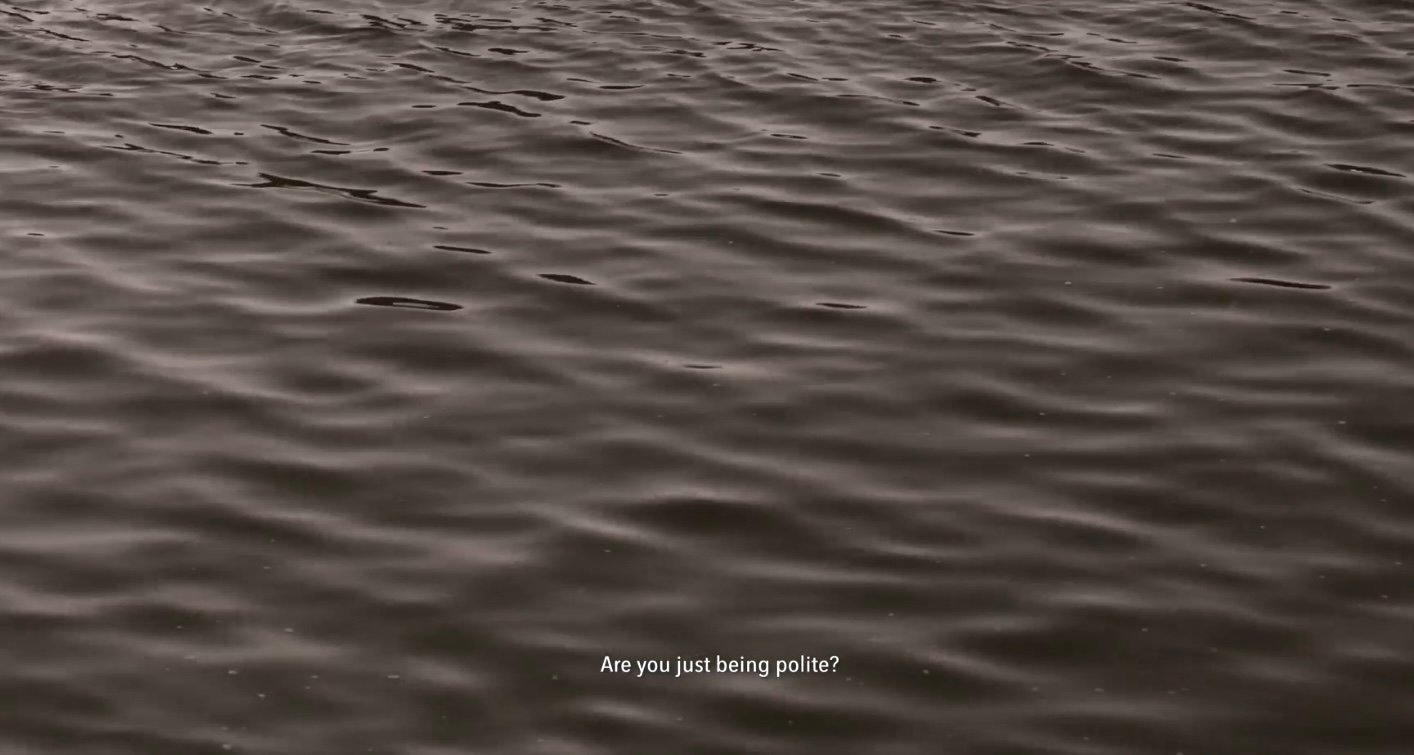
〈河畔煙火〉作品截圖
彩色4K錄像作品
11mins10se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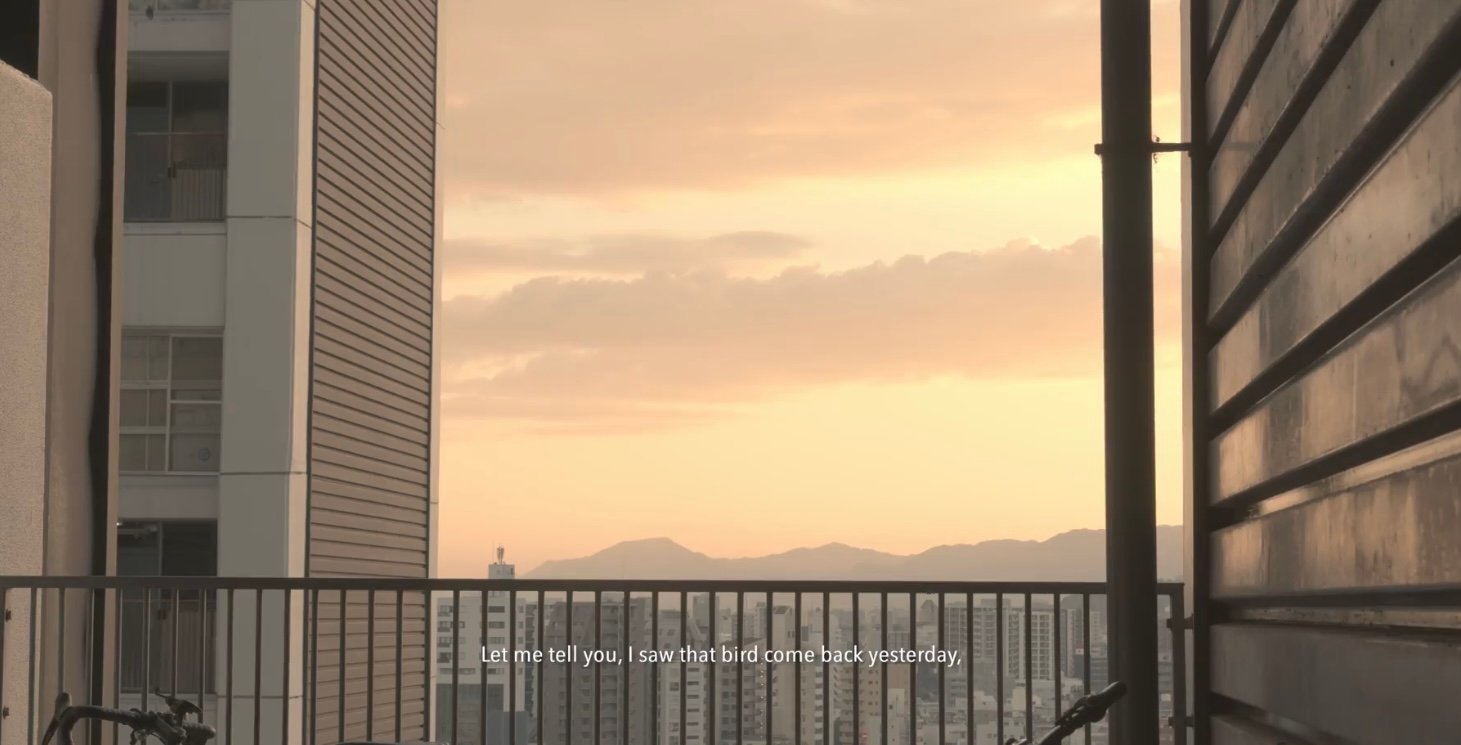
〈河畔煙火〉作品截圖
彩色4K錄像作品
11mins10sec
這種在更大的歷史脈絡中描繪個人、微小時刻的嘗試,或許在他在廣島製作的影像作品〈河畔煙火〉(Riverside Fireworks)中更為明顯。2023年,糖果鳥在廣島停留約一週,在基町地區進行拍攝。這個毗鄰廣島城的地區曾經是軍事設施所在地。距離原爆圓頂堂僅一公里,這裏在1945年8月6日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後來被改建為原爆倖存者的臨時住宅區。隨著人們從日本前殖民地返回,或是新來者為了在戰後重建期間尋找工作而來到廣島,住房需求不斷增加。在流經基町地區的太田川河岸,非法房屋不斷增多,惡化的居住條件最終導致該地區被稱為「原子貧民窟」。糖果鳥所停留的基町高層公寓,是1970年代後期作為重建計畫的一部分而建造的,以清除這些不適合居住的建築。在鼎盛時期,這裡居住著超過一萬人。如今,該地區呈現人口老化和文化多樣性增加的特徵,連接公寓的商場中有著顯眼的中國餐館和雜貨店。在基町地區,糖果鳥創作了一部影片,特寫了來自不同國籍和背景的人們:在不同時期來到日本的一個中國男人和女人、一位在日韓裔男子,以及一位日本女性。影片敘述了一對男女試圖在時光流逝後重逢的故事。然而,由於同一角色由不同演員扮演,他們聲調和口音的細微差異,讓觀眾開始質疑:眼前所見的是否為同一個隨時間改變的人?抑或是來自不同時空的陌生靈魂?詩句巧妙地編織在影片之中,雖然輕盈地觸及廣島的歷史創傷,卻又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讓這些暗示如晨霧般難以捕捉。基町的日常場景、普通房間中熟悉細節的鏡頭,即使影像清晰,卻留下了某種模糊的印象。這種模糊感似乎源於這些細節很少透露居住在這裡的人們的特徵或背景。即使出現建築物的鏡頭,也是從自然的視角拍攝,避免超出人眼所能看到的極廣角或鳥瞰視角。儘管〈河畔煙火〉結合了基町的景象和聲音,但它創造了一個具有漂浮感的世界——不固著於任何特定的地點或時間。這也許源於糖果鳥堅持保持一種個人的、近乎苦行的視角,避免普遍化,而是立基於親密的、個人的視角。
_壓克力、畫布_33×45.5cm-1.jpg)
(一)
壓克力、畫布
33×45.5cm
當我觀察糖果鳥作品的這些特質時,讓我想起美國詩人梅·薩頓(May Sarton)1970年9月15日的日記,開頭寫著「從這裡開始,下雨了。」薩頓繼續寫道:
數週以來,我第一次獨自在這裡,終於要重拾我的「真實」生活。這就是奇怪之處——朋友們,甚至熱烈的愛情,都不是我的真實生活,除非有獨處的時間去探索和發現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沒有這些既滋養又令人發狂的打擾,這種生活會變得乾涸。然而,只有當我獨自在這裡,「房子和我恢復舊日的對話」時,我才能完全品味它。
這篇日記寫於薩頓因在小說中揭露其性傾向而失去大學教職,與周遭世界保持距離的一年。她經歷了個人的損失,包括與愛人分離和父親的離世;她搬入鄉村的家,在花園工作並面對內在自我。這一年的日記捕捉了深刻的個人視角、日常生活和更廣闊世界的交匯點——這種交織只能透過日記的形式來傳達。她表達需要獨處「去探索和發現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的句子,在糖果鳥的作品中產生共鳴。這些作品似乎是在面對空白畫布的房間裡,或是在日常生活中獨自編寫劇本時,對世界正在發生的事的探索——或許糖果鳥的作品可以被描述為「日記藝術」。正如薩頓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寫,日記/日誌是「找出我真正在哪裡的方式」[2]。與需要更謹慎和詳細結構的小說不同,日記提供了以分散、零碎方式表達各種想法的自由。拔除雜草、陽台上築巢的鳥兒、茶壺中腐爛的茶葉,以及空椅子的存在等故事都相互連結,暗示著超越自身的事物。
_2024_壓克力顏料、油畫板_27x35cm.jpg)
(十九)
2024
壓克力顏料、油畫板
27x35cm
用寫作者熟悉的日常語言書寫也是日記的一個特點。有時,它感覺像是與自己的對話。說到日常語言,日本有許多方言,在廣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詞是「waya」。這個詞意味著「混亂」或「雜亂」,可以用來描述從凌亂的房間到被轟炸摧毀的城市等任何事物。這個詞也經常用於描述意外發生的事情,不論事件的規模大小。當居住在廣島基町——這個經歷過許多艱難的地區——的人們說出「waya」這個詞時,我在其中看到一種力量,一種韌性,因為他們用簡單的「Waya-jane(好亂啊)」來概括他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在我們的生活中,每個人都會遇到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完全用語言表達的經驗和事件。當我們在經歷這些經驗後努力繼續生活時,有時會對可用來表達的詞彙或方法的不足感到絕望。在「waya」這個詞的簡單中,我感受到一種態度:一種接受無法表達之事物的本然,一種思考他們所處情境,吸收或釋放周遭發生事物的態度——這屬於普通人。
_壓克力、畫布_38×45.5cm-2.jpg)
(三)
壓克力、畫布
38×45.5cm
創作藝術是對敘事方法的持續探索——尋找適當的方式講述自己故事,以及掌握自己想要傳達之事物的輪廓。糖果鳥的作品反映了這種試錯過程。他從塗鴉轉向影像創作的歷程,體現了他不斷探索能夠與其創作理念產生共鳴的媒材。塗鴉——通常規模較大、公開性強,且帶有強烈的訊息或象徵意義——與展示在螢幕上或畫布上的繪畫或影像有很大的不同,後者規模較小。繪畫和影像也允許藝術家展示一系列更個人或抽象的隨機影像,這些影像沒有象徵性的力量。然而,在這種小巧中,我們找到了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有時會邀請我們想像更宏大的事物,揭示周遭世界意想不到的面向。即使可能感覺渺小或脆弱,只有通過細心地與周遭世界互動並深化我們的內在生活,才能看到世界的這些片段。糖果鳥的作品就像微小的低語,引導我們獲得對這個世界的視角。仔細聆聽這些低語和我們自己的內在聲音,將引領我們切實地在這個世界中創造並找到自身的位置。
_2024_壓克力、畫布_65x53cm_大.jpg)
(十四)
2024
壓克力、畫布
65x53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