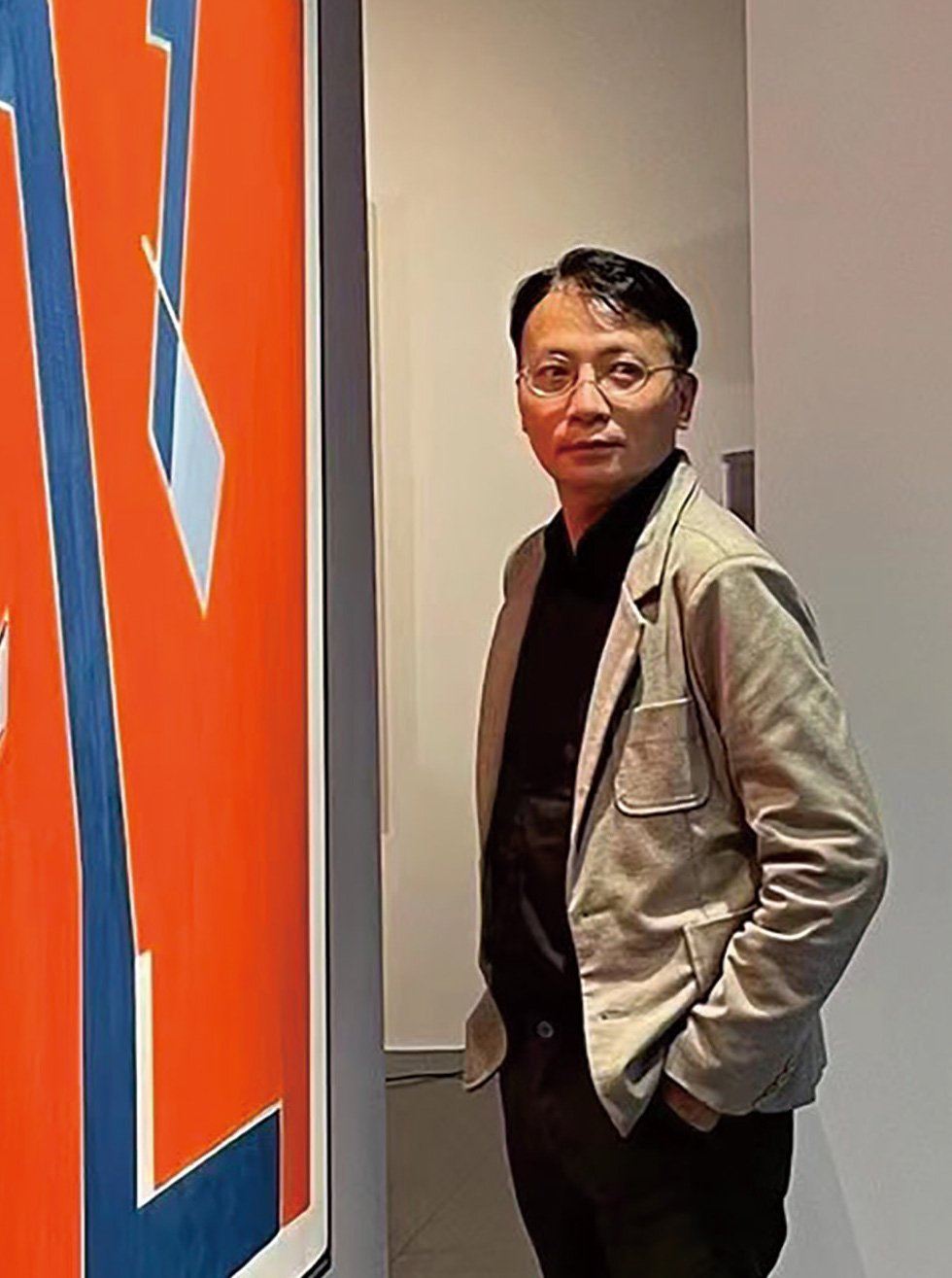疫情時代
策展人更像一位礦工
鄭乃銘 / 專訪
圖片提供 / 王焜生
如果真有一種統計數據,統計目前地表最忙碌的策展人有誰?那,無疑地;王焜生絕對是排在前三;也有可能是居於第一!
再沒有一位獨立策展人能夠像他,從疫情時代進入後疫情時代,始終維持滿滿的策展能量,一直持續他對於構思展覽、重新發掘藝術家新質量、陳述藝術作品的正能量。

2021/12/6 – 2022/3/13 高雄市立美術館湖畔廣場
2021/12/6 – 2022/1/17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2021/12/6 – 2022/3/13 中鋼總部大樓戶外空間
但是,王焜生面對自己如此高密度策展事務的反應說法倒是令人噴飯。他說「真的太誇張了!我自己都覺得多的太誇張了」!「仔細想想,以今年上半年平均來看,我『似乎』真的是一個月做一個展覽(編註:實際數量是12個)」!「以前,真的沒有覺得那麼忙,可能是因為疫情之前;我通常有固定出國週期,很自然在台灣的時間就算得出來。疫情發生之後,不可能隨意移動,留在台灣的時間相對多,自己也會覺得該做點什麼。因此,對比之下就發現這二年多;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很明顯時間都被工作佔得很滿」。「疫情發生以來,我們其實都很明顯感受到藝術展覽或活動相對激增。我在想,這或許某種程度也反映大家都有共同的慌張心理;藝術家如此、觀眾也如是。畢竟,大家都沒有這樣的經驗是共同面對如此嚴峻的疫情發生。當大家都困在固定地方,生活的形式、心理的壓力;都在產生變化。但是,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倒是覺得我們不應該浪費這場疫情給的危機,疫情相對之下也讓我們;在藝術產業的我們,有了一個不一樣檢視自己過往與眺望未來的轉機」。

2022/2/19 – 3/27 異雲書屋

2022/5/6 – 6/30 正修科技大學 藝文中心
王焜生說「因為你問起,也讓我有機會重新回過頭去想想這近三年藝術環境、策展人有了什麼樣的改變。我稍稍歸納出來幾點:一、藝術展覽從實體走向線上,儘管後來我們也發現線上展覽依舊存在若干問題,無法真正契合藝術與人的交流。但是,你不能否認;線上展覽在這三年被藝術單位、組織廣泛運用所帶來的社會性。二、年輕藝術受眾激增。這一點可以從兩個結構來談,一個是純粹的欣賞人口;另一個則是所謂年輕藏家勢力的興起。我個人認為,由於疫情使然,許多原本在國外受教育、生活的二代,都因為父母的關切與擔憂而被叫回到台灣。這些人是這三年藝術生態表現轉變的最大推力。我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基於這群人都與上一代、上上一代對待藝術的眼光與態度,甚至參與的心理,有著180度改變。他們都具有社群聚眾能力,這些人看展覽是像骨牌效應,彼此牽扯也相互帶動,對他們來說;也許一開始親近藝術活動是在藝術博覽會,後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美術館、畫廊的活動,你都能夠看到年輕族群是一波波湧入。最早,他們習慣打卡、分享,形成社群概念。雖然,這樣的情況現在依舊存在,但也發現他們不僅僅只是如此,他們更積極涉入藝術的活動、講座,也因為有消費能力。對!沒有錯!我們等了10、20年的小孩,現在都長大了。他們也都有自己對藝術的眼光,也有經濟基礎具備了消費能力。他們與過去的藏家最大的不同是心態開放、且樂於分享。看展覽、購買藝術品,完全不會偷偷的來,反而都能在自己社群造成眾所週知的效應。我個人覺得,私人畫廊除了在疫情最開始第一年營運顯得噤若寒蟬之外,嚴格算是這二年畫廊;無論國內外,之所以展覽比率頻繁,跟年輕受眾所帶起的藝術關注影響力有著絕對大的關係。你可以從台灣不少畫廊換展速度高,且開幕都能帶來滿滿年輕觀眾;不難得知新藏家影響力確實已經存在。我們且不去談年輕族群對當代藝術是比較偏重於藝術商品化、著重視覺療癒,但在疫情發生的這段期間,藝術生態迅速完成世代交替的事實,這股力量在以後發展更是不容小覷」。

2022/1/8 – 4/9 藝非凡美術館

2022/4/16 – 6/11 新思惟人文空間
王焜生再說「我回到自己的策展人角色,我比較想跟你分享是策展人面對策展質量心理的不同。以前,策展人總是依循命題下羅織作品,但我在這段期間面對策展這項工作,我反倒更著重是在對『人』的再發現與再定義。我舉二個例子說,在異雲書屋的梁兆熙展覽,過去太多策展角度與論述都指向他作品愁苦、鬱鬱,可是,我根本不覺得他的藝術跟愁苦有何關係?我反而感受他沉溺在創作的自由與清歡。我於是轉了很大摺度,點出他作品的這份特質,大大改變過去眾人對他作品的認識。結果,這個展覽異軍突起達到相當不錯的成績,也吸引了不少質優新藏家!高美館的【抽象高雄】一開始就標明不是爬梳高雄的抽象繪畫史,我要做的是以高雄為中心點,藝術家不是主角,我要讓大家看的是藝術家在這個地區生活,卻始終沒有讓人真正看到自己是如何在形塑這個地區。作品沒有所謂量身訂製,都是從美術館庫房、藝術家工作室慢慢挑出來。結果,這個展覽又改變了對高雄既定印象,卻讓大家發現高雄前所未有活力與張力,還有藝術家最細膩的真情」。「我想講的是,策展人老是被要求做點深度的展覽、要去跟藝術家談…,但我發現自己並沒有那麼依照規定去跟藝術家談話。同樣;什麼是深度?深度不是去討論作品、不是命題、不是論述寫得艱澀難懂,深度是要回到藝術家本身及作品本質,策展人應該要重度去發掘藝術家創作最純粹的那個部分,是要將那個部分拿出來給觀眾看,讓大家重新認識這位藝術家、理當受到認識卻在過去被忽視的那個質地。比如說,在藝非凡美術館的【陳聖頌個展】,就讓大家正視到這位藝術家一路蘊積的非凡能量」。

2022/04/23 – 11/27
Personal structure 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
最後,王焜生說「疫情,讓大家見面成為奢侈,封閉的定點;表面上似乎把距離給調近了。從藝術生態的角度來看,我們好像因為這個關係而讓自己更有機會接近藝術,形式上距離是近;但這是否表示我們真的懂了嗎?你問我;疫情前後策展人是否有了什麼樣的改變或不同?我覺得,是有不同。至少,我在面對策展的工作,在心理上是不同。我更樂於去把『人』提現出來,讓觀眾能認識這個『人』。當你學會了認識『人』之後,很自然就會讀進關於這個『人』的創作裡」。

2022/3/12 – 5/15 上海東畫廊
王焜生 協同策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