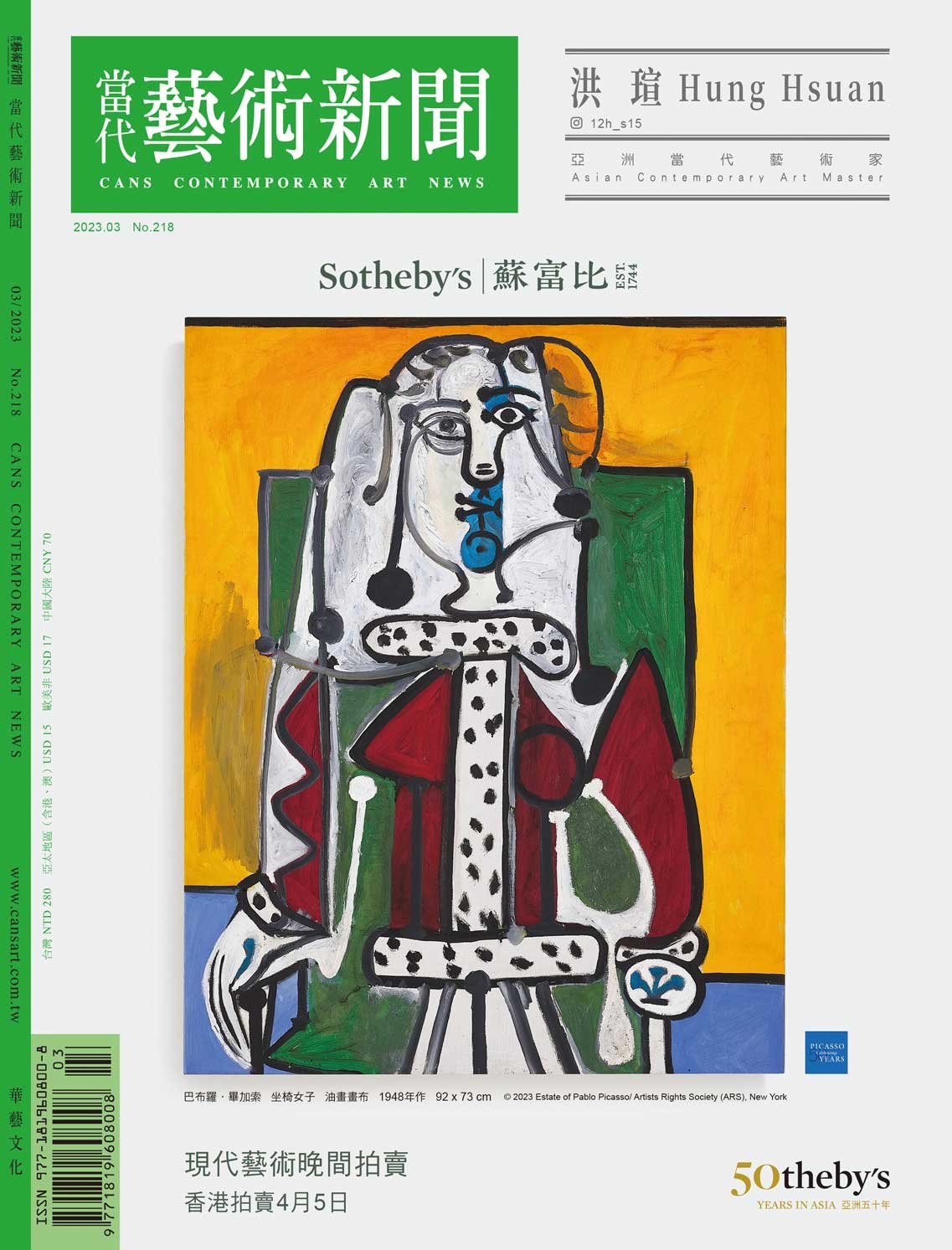歲月在他面前無法遁形
寫給楊北辰
文/鄭乃銘
圖片提供/采泥藝術
對於楊北辰跟他所選擇的創作媒材,總會讓我很直接就想到席慕蓉這首詩! 我總覺得,楊北辰選擇木材來作為創作材料,那並非是樁偶然的事件;那是一份藝術家跟材質本身的緣分。而這樣的緣分,又因為兩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來「解釋」時間,這個共契無形間造就這般相遇。
楊北辰是一位擅於將餘溫鎖進歲月裡的藝術家。
但最關鍵的是,楊北辰的藝術無關人、也不是描繪人,卻處處都能感受到人的體溫;一種曾經歷過、但爾今則轉手的餘溫輕迴。
我常會這樣看他的藝術。他固然選擇的媒材是堅毅沉默的木頭材質,問題是;他卻擅長將木訥轉化成為溫熱,一種未必燙傷人,卻相對能濕潤眼眸的溫度,逼使得觀者對著作品,從初見的不可思議到細細端詳的百感交集,心理層次的轉折,激盪出作品與觀看者的互動,是最令人百看不厭的內心戲!
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陽光下慎重地開滿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節錄自席慕蓉〈一棵開花的樹〉

謄刻古籍 No. 17 –“觀察者”
Transcribe Ancient Books XVII - “The Spectator”
桂楠木、油畫顏料、凡尼斯
單本尺寸範圍:17 x 10.7 x 2.9 cm x 8 本一套
2020
825年歷史的大學舊圖書館
開啟他對古籍宿世曾有過承諾
「我一直記憶深刻是首次踏入學校舊圖書館時,那整個腦子就這樣炸開般的感覺」。楊北辰說。
1999年他進入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繼續深造,這是歐洲相當古老的一所大學。它的圖書館分成兩結構:舊大樓是舊書古籍、新大樓自然是現代的圖書資料。楊北辰初來乍到踏入舊圖書館大樓時,徹底被歲月給收服。自此,甘心為歲月「服務」。
這位原本就喜歡閱讀的藝術家,這個之前對所謂古籍善本的概念,基礎上還建立在極度東方竹簡、線裝…等等印象當中。問題是,西方的古籍又全然不像東方文化這般面貌。多數的古籍以皮革為封面、紙頁採是很傳統手工模造紙,線裝;自然是很基本的。只是讓楊北辰相當震驚的是,眼前的古籍,動輒是百年或數十載的時間刻度,可是,面對這些古籍卻讓他深深確確感受到;這本書在經過那麼長時間、也勢必經歷過不少人翻過;甚至擁有過。但是,書所散發出來的餘溫,清清楚楚就這麼散開來。甚至,舊書特有味道,瀰漫在整個空間裡。
那個時候他才深切明白,歲月不是過了就沒了。歲月會留下餘溫、歲月是會有味道的。
那來自對古籍的悸動,也許是一份他自己都解釋不出宿世承諾,就這麼被喚醒。

謄刻古籍 No. 20 –
“莎士比亞作品集”
Transcribe Ancient Books XX-
“ Shakespeare's Plays”
桂楠木、油畫顏料、凡尼斯
20.5 x 13.5 x 4.5 cm
2021~2022
年少是炫技 長大後則只想藏技
我跟楊北辰坦白告解對他早期的木雕創作,沒有太深刻感受,也始終走不太進去那些作品裡。那個時候,他雕刻公事包、鞋子、外衣…。我說;這些物件就是物件,就這樣…!
沒料到,楊北辰聽畢,絲毫不以為忤,反而大笑不已。
他倒是回了我一段話,令我對眼前這位相識已久的藝術家更另眼相看。「就像您講的,創作的初期,我還年輕;那個時間你會想要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可以、能夠做。但,再進去一點的想法,不是沒想,應該是還沒想透。對當時的我來講,這些物件當然都是經歷過人的痕跡、具備時間的經歷,我很努力去把物件本身的外像擬真化,像;是重點」。「但現在想,這就好像年輕的時候,會很在乎人家有沒有看到你?會有一股很迫不及待想讓人知道你會什麼。如果說,年少是一種炫技,那麼現在的我;則更想要藏技」。「因為,面對古籍這個題材,我終究明白;歲月其實不需要敲鑼打鼓宣告示人,歲月;無論你喜不喜歡,它終究會在你身邊」。這段話,更也說明本事是可以熬、可以捧,捧著熬著;本事也就長出來了。
自此,楊北辰雕刻古籍,其實是在雕刻歲月。所謂藏技,更也只是因為歲月總是躲在生命後面。

謄刻古籍 No. 15 –“新約聖經”
Transcribe Ancient Books XV-
“Biblia Testaments”
桂楠木、油畫顏料、凡尼斯
27.8 x 23 x 9 cm
2020
材料處處都見歲月鑿痕
卻也未必樣樣都能留存
楊北辰所選擇的木材,完全與保育樹種或珍貴樹材徹底絕緣。他採用的是普通到不能普通的桂楠。
他說「對於選擇木材作為創作的人來講,他所面對的材料,事實上就是一整棵樹,不是一片木材」。
原來,樹的中心部位,並不適合作為雕刻。因為,容易裂。樹的最外圍那一圈,則壓根不能採用。唯一能用的,就只有樹的中間層木質部」。「再來深透一點想,能夠長成一棵足堪被拿來使用、作為創作材料的樹,哪一棵不是百年身」。「在這當中,物件;也就是被描述的主體,它本身就已經具備時間感。雕刻的工時,本身也得要有時間。樹木,更需要時間來等待。觀眾在面對完成的作品,從初看的驚訝到錯覺眼前是真物、再到終於看出個究竟,這也是得要有時間。對時間所進行的仿真感,無不緊緊相扣在任一環節裡」。
「你還記得2022年我跟『大摩』首次合作,你突然跟我說,陳年威士忌酒桶與我古籍木雕創作,在精神與材質都是一氣相通。我那個時候聽了,真的是雞皮疙瘩竄起。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人家能那麼簡潔就點出我作品的內底」。

謄刻古籍 No. 23 –“法蘭西學院辭典”
Transcribe Ancient Books XX III-
“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桂楠木、油畫顏料、凡尼斯
A~K 27 x 21.7 x 5.6 cm
L~Z 27 x 21.7 x 6 cm
2021–2022
從事古籍木雕創作 才深刻體會原來歲月是會呼吸的
我對楊北辰古籍木雕創作特別想要提及二個關鍵點是…
- 材質與技巧達到一種神乎其技的共識。楊北辰心思極度纖細敏感,但他並沒有花太多口舌去演繹自己對創作上的深度鑿痕,但卻花了相當用心的時間去把內心對古籍本質性特色「刻劃」了出來。我相當喜歡這種不是說得一嘴好作品的人!他對於材質的用心,完全印證到每個創作細節上。木質本身即便是它被砍伐之後,拿來作為生活物件的素材,但很少人真正會去洞悉這些所謂木質,事實上是處於一種「偽死亡」情態底下。也就是說,木質會隨著時間流動,還是擁有極為緩速的呼吸節奏,而木質本身的毛細孔、它的纖維,會隨季節、溫度而出現表面上質變,甚至都會相對吸收外在環境的改變。楊北辰就細膩捕捉到這個變化,而且;全把它留在作品身上。過去傳統手工造紙,觸感所傳遞的量體,很容易讓使用的人感受到材質生命是被留在紙感上。油墨的氣味與紙張本身的氣味,層次分明。接著,人手觸摸、翻閱,書會記錄著人的慣性,紙面的汗漬,或有人習慣沾一下口水好方便翻閱紙頁,濕氣/風乾,會讓書頁邊角捲曲,也都依附在紙面上。再來,一本書放存在不同的空間,空間的溫差也都反映到書上。空間一旦過潮,紙面或者古籍上的皮革封面、書背,都會或多或少出現黴菌。黴菌,在當下沒處理,時間一久;就會留下暗黑痕跡,更難被洗除。楊北辰竟然能一個個一環環,把這些古籍本身經歷過的時間、空間、人為,絲毫不含糊詳載到一冊冊古籍!木質本身的揮發度,此刻似乎是來服務於這位藝術家,而且是來貼近這位藝術家纖細感情。木質的原生模樣,已被這位藝術家降低到最低。
- 歲月隱藏的光澤,原來是被擦出來。西方古籍多數會以羊皮作為封面,皮革;根本是一個活體。尤其是接觸或者撫摸的人越多,皮革隱藏在內部的光澤就會被釋放出來。楊北辰的古籍木雕最「可怕」細節之處,也在於他完全不是靠著上色來呈現光澤、那份油光。而且,他也不採用在表面塗上凡尼斯。因為,凡尼斯容易讓古籍的真實感整個降低。他告訴我,「我就隨意拿一小塊木頭削光,就靠著這小木頭不斷又不斷抹擦著古籍雕刻的封面,所謂由木來引出光澤,就這樣出現」。這也就是說,木質本身的油質來帶出另外一個木質的油質,讓歲月就這麼被抹擦現形。甚或是皮革曾因受潮又變乾之後,皮質會變硬、表面會起皺,楊北辰連這樣的小細節都容不得苟且忽略。我想,時間固然會被熬乾、歲月也可能被磨疲,人對傳統閱讀的興致,儘管已被電子化取代,但書本所承載的知識是經得起淬鍊,一如古籍內蘊的那份光澤,就這麼的被楊北辰一點一點抹擦了出來。

謄刻古籍 No. 14 –
“新約聖經/詩篇”
Transcribe Ancient Books X IV-
“ Het Nieuwe Testament
/ Het Boek der Psalmen”
桂楠木、油畫顏料、凡尼斯
18 x 11.5 x 8 cm
2020
藝術走到後來 其實就是人對自己的實踐
楊北辰讓自己的創作,成就的不單單只是藝術。
我總認為,他讓自己的作品都具有靈魂的份量。這點,始終令我很感動不已。 如果說,創作初期的物件雕刻是具有重量,那是因為他所選擇的題材,本身就具有量體的重度。但,書?固然也具有量體,但,書;更多的是知識的承載,更多的是時代的微型文化思維,它所含蘊的是份量,而不是稱斤論兩的重量。 楊北辰把這兩種「量」闡述得極為明晰。
他說「我未曾想過要刻一本展開的書。因為,一旦你把書攤開,關注的焦點就會在書到底寫了什麼內容?是什麼文字/語文?那根本不是我創作古籍系列的原初」。「一本本闔上的古籍,在我眼裡,那形同是文化紀念碑,那更能融入歲月裡」。
文化符號也同時能記錄時代的異化過程,這點在他幾件作品出現白色痕跡可看出箇中含意。他說「白色,是我對這三年疫情最深刻印象。過去,我們提到白色,會覺得聖潔、單純、尊榮。但曾幾何時白色在三年疫情期間對所有人都是不好的印象。方艙醫院、大白…白色在疫情成為某種偽善、威權、焦慮的象徵。我於是在作品出現白色,用意就是紀錄這個時間的心情」。
藝術家能悟透材料的本質,絕對是將材料精神與創作心思共同交融的先決條件。藝術,在這個時候不僅僅只是一種創作,它何嘗不是人對於自己的充分實踐。
楊北辰就印證了這個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