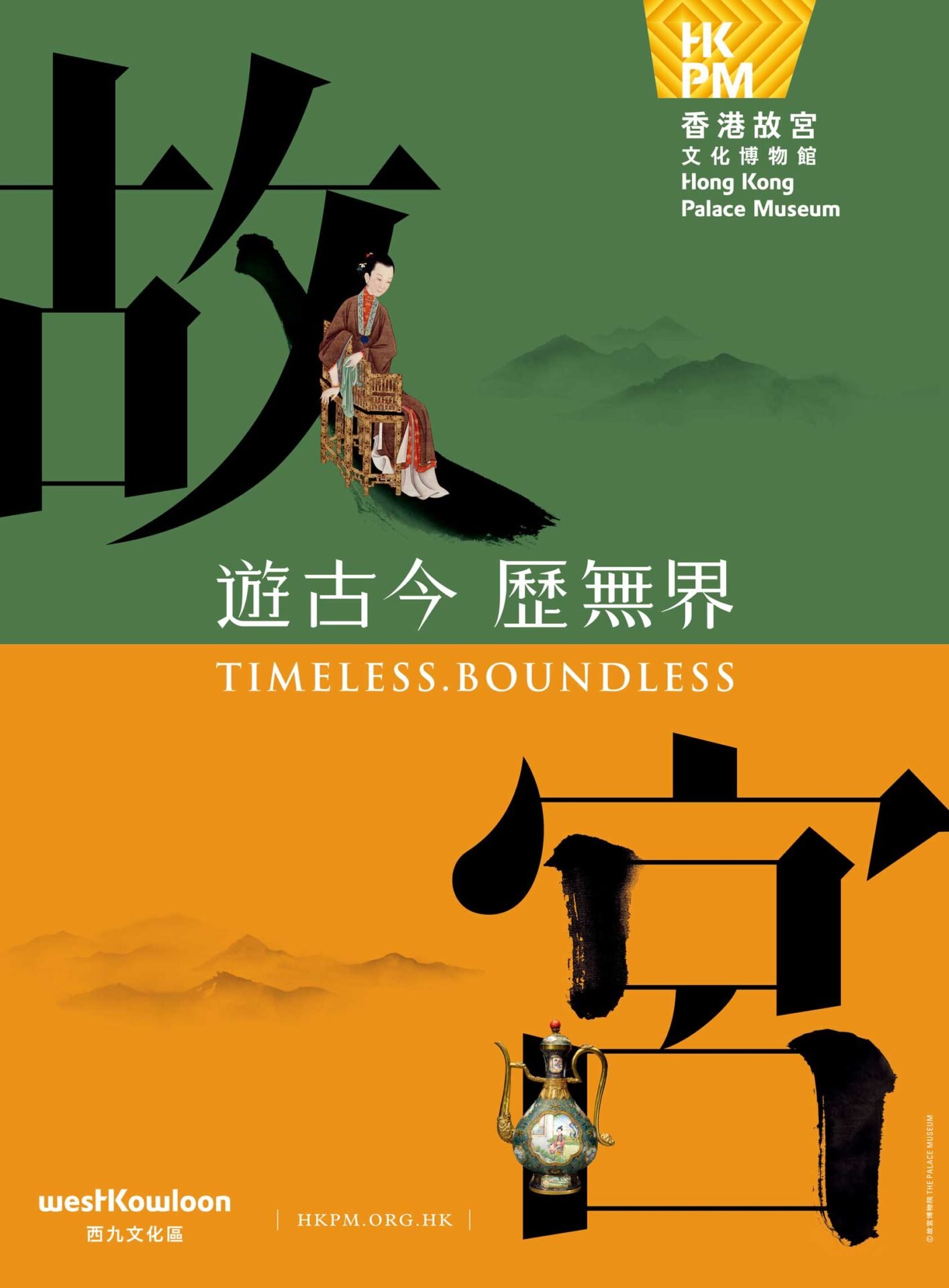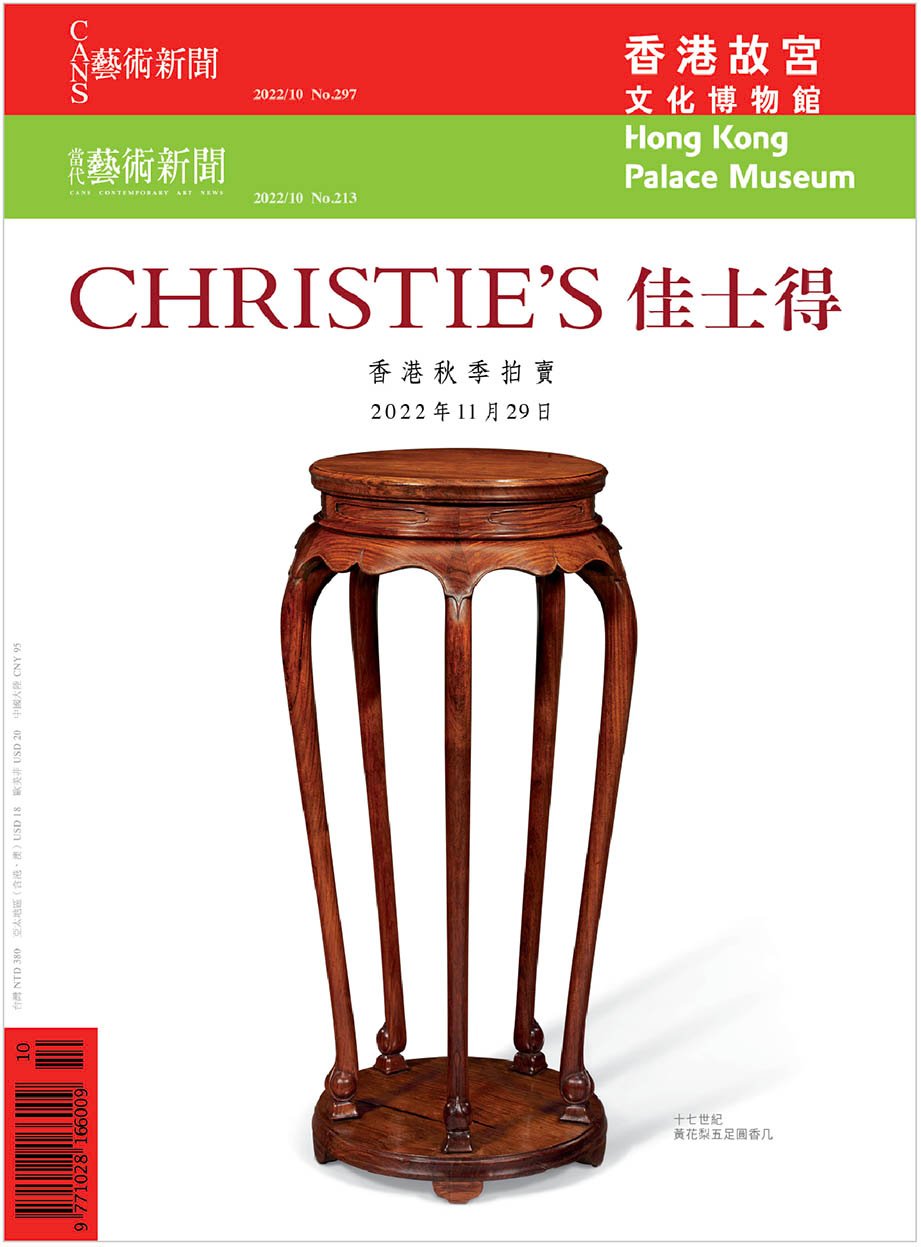田本芬 / 香港專訪
圖片提供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焦天龍博士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首席研究員,他於2021年3月16日履新,負責發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品、展覽及出版方面的策略規劃。
焦天龍博士的專長為中國考古與藝術史,在香港及美國擁有逾20年策展經驗。分別獲北京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頒授學士及博士學位。在加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前,他曾為多間主要博物館主持學術工作,包括美國畢士普博物館太平洋展廳及丹佛美術博物館亞洲藝術展廳的重置工程。他亦曾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美國和中美洲等地從事和主持考古發掘研究。他以中、英文發表專著和合著七本、及論文九十餘篇,其英文專著《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Cambria Press 2007) 獲美國 2007年度 Philip and Eugenia Cho亞洲研究傑出成果獎。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表示:「焦博士豐富廣泛的研究策展背景和高度認可的學術成就,對我們創建一流的博物館、從而吸引香港以至世界各地觀眾到訪,以及向全球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極之重要。」
《CANS藝術新聞》很榮幸在香港專訪到焦天龍博士。就如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吳志華館長所言:「我們十分高興焦博士重回香港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籌建工作。焦博士在研究和策展方面的豐富經驗。」此次專訪焦博士深入的談到參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籌建工作,及該博物館策展方向及未來發展,以下便是精彩的專訪內容。

在中西博物館 擁有極高聲譽的焦天龍博士
CANS藝術新聞:您之前的職場經驗都在美國,這次為何會回到亞洲,又為何來到香港故宮?
焦天龍博士:我是山東人,北京大學考古系完成學士學位之後,在北京社科院做了一段時間的考古研究。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博士,我的指導教授是張光直教授,張教授曾任哈佛與耶魯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2003-2013年這十年我到了夏威夷,擔任夏威夷畢士普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並兼任夏威夷大學兼職教授、廈門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客座教授。2013-2014年間回到亞洲,擔任香港海事博物館總館長。2014-2015年間擔任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中國部主任及研究員,參與了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建館50周年紀念的【皇帝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大展。2015-2021年間擔任美國丹佛美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丹佛美術館是美國前七位的大型綜合博物館,後來香港故宮籌備時就把我挖過來了。我的職業生涯大半在美國,事實上我人生的大半都是在美國。在美國最大博物館做美術史研究,老一輩的學者都已凋零,目前美國各大博物館的亞洲藝術,基本上都已經是我們這代人接手。
香港曾是我的家,所以我很高興能夠回到香港工作,而且我很榮幸可以加入香港故宮這個充滿活力的研究員團隊。我深信香港故宮能在世界各地認識中國文化和藝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並期待與團隊合作,為這所重要的博物館邁向成功作出貢獻。

CANS藝術新聞:中西博物館任職經驗相當豐富的您,除了香港故宮,過去您是否還參與博物館的興建過程?
焦天龍博士:香港故宮從動土到完成共歷時五年。因為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面爆發後,工程受到延宕,當我2021年3月來港履職時,這裡還是一片建築工地。去年疫情開始逐漸趨緩社會開始恢復正常運作,開工後1000多位工人全力加緊趕工,就這麼一年,香港故宮達成預定的目標,在6月22日正式開幕展出,這種效率真可以說上是奇跡。在新冠疫情期間全球有好多博物館倒閉或者暫停營運,我們正好逆襲道而行,不但開幕了,還一炮而紅的迎來好彩頭,開幕至今真的是一票難求,這是疫情期間全世界博物館少見的現象。

香港故宮 策展方向及未來發展
CANS藝術新聞:香港故宮以「故宮」冠名,可見其定位與規格。但香港故宮本身並沒有太多的館藏品,這次開幕展的展品,看來都是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屬性是否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為主?
焦天龍博士:我們博物館全名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簡稱「香港故宮」。香港故宮不隸屬北京故宮,也不是北京故宮的分支,香港故宮的展覽規劃主導權還是在香港,和香港M+一樣,都是隸屬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下的子公司。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08年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所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發展西九龍文化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公營組織,管治架構由董事局、委員會、附屬公司及諮詢會組成。西九文化局旗下管理的許多公司,像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西九文化區文化中心、戲曲中心…等等。所以香港故宮無論在行政上,財政上,都是完全獨立的,只是名稱為「香港故宮」。 香港故宮的建設,包括了建造及展覽和活動策劃等所有費用耗資逾30億港元,政府沒有出資,全部是由香港賽馬會捐助。雖然它不隸屬香港政府,與港府沒有實質上的關係,但是方方面面千絲萬縷的聯繫又離不開香港政府。 開館展出的作品的確是來自北京故宮,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收藏,例如在第六展廳所展出的【同賞共樂 — 穿越香港收藏史】展,就有部分展品是香港故宮的館藏。香港故宮的創建以來收藏已經有1000多件,全都是來自香港收藏家們的捐贈。眾所周知,香港收藏家的收藏實力享譽國際,他們的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都展覽過。香港收藏家們都非常支持香港故宮,目前接受的捐贈,都是來自幾位全球知名的香港收藏家的重要收藏,像「夢蝶軒」。「夢蝶軒」所捐贈的這些金銀器,已經讓香港故宮在全球同類的收藏名列前茅了!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其他藏家的捐贈。

目前與未來展覽
CANS藝術新聞:目前香港故宮有九個展廳,第六、第七規劃是「香港廳」,其他展廳分別有特定的展覽規劃與想法嗎?開幕展後接下來會有什麼樣新的展覽?
焦天龍博士:香港故宮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立足香港、面向中國、面向世界,推動中華文化,向世人介紹推動中華文化為理念,同時與世界對話,開幕展的九大展覽便圍繞著這些使命而來。首先香港故宮與北京故宮著深厚的戰略合作,我們與北京故宮簽訂的開幕展便是以北京故宮所藏文物為主,所以九個展廳有七個展廳,基本上都是來自北京故宮展品。第九展廳【馳騁天下 — 馬文化藝術展】雖然也是與北京故宮合作,但也有巴黎羅浮宮的藏品,更多了與世界文明的對話。
百餘年來香港是中西文化的橋樑,立足香港、面向世界,便是我們的策展方向,我們嘗試用不同的視角,與西方對話。對話的整個主題不一樣,對話發展方式就不一樣,對話的故事線也不一樣。我們的團隊網羅了文博界的菁英,素質也是很高的,確立主題後,我們將發展出很多「古今對話」的討論。尤其是第五展廳【器惟求新 — 當代設計對話古代工藝】展是比較有創意的展覽,將傳統中國古代文物的工藝品設計,與香港當代設計工藝進行對話,呈現出文化傳承與時代特色。

CANS藝術新聞:除了與北京故宮達成戰略合作外,未來也會跟像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等西方博物館合作展覽嗎?
焦天龍博士:開幕展,由我方香港故宮策展主題確認後,北京故宮方面則有一個團隊對接。每一個展廳的展覽,都有不同對接的團隊。中國內地的博物館,我們都保持聯繫,海外知名的大博物館也是,我們很願意與各大博物館進行交流,未來也會有合作的計劃。中西文化藝術交流是一個新的戰略思維,這也是香港故宮的未來。

CANS藝術新聞:許多博物館都有分成器物、書畫不同的展廳,每個展廳還有獨立的團隊來思考策展,甚至每年選定一個月份推出像年度特展,香港故宮有這方面的規劃嗎?
焦天龍博士:每個展廳因為展品條件的不同,所以展出的時間也不同。一般而言,器物比較能長期展出,書畫尤其是古代書畫,這些珍貴的絹本、綾本古代書畫只能展出三個月,就得定期更換。像是第八展廳「國之瑰寶 — 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這些國寶書畫限展時間是一個月,開幕迄今已經換了兩次,馬上要換第三次了。全館展覽分為定期展與不定期展,時間比較不一定,我們也計畫大型展覽展。像是第八、第九展廳是特展廳,三個月至六個月就會換新展。年度大展我們已經排到三年後了,今年11月將要展出與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共同策展的【藝苑尋珍——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名品】特別展覽。北京故宮、台北故宮也都曾展出西方油畫大師作品,如同剛才所說的「古今對話」,博物館只展出中國藝術似乎有點狹隘。目前第九展廳【馳騁天下 — 馬文化藝術展】,便同時展出西亞、歐洲大陸的藝術品,這就是我們強調的「中西對話」。
CANS藝術新聞:未來的展覽方向,全館會以一個大主題為主軸,再分為子展覽?比如臺北故宮的「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整合各個博物館及跨部門合作的大展?
焦天龍博士:我們開幕展覽就是如此,除了第三展廳陶瓷廳展出歷代陶瓷,其他展廳都圍繞著主題展開,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故事線來串連呼應這個主題。我們團隊間不存在有些博物館各部門的森嚴壁壘,所以北京故宮對應的團隊也是如此。

專家編制
CANS藝術新聞:作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首席研究員,香港故宮研究部門設定的品類與規模有多大?各位專家全來自香港嗎?現今策展團隊有多少人?
焦天龍博士:我們研究員的人才不侷限於香港本地,而是來自四面八方,只要各領域好的人才我們都歡迎。像是周維強博士,他是臺灣清華大學畢業,原來任職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另外一位研究員蔣得莊博士,她是清代宮廷藝術專家,她也是在臺灣長大,英國讀書,當然還有來自北京與中國各地的專家。目前策展團隊近20人,之前我們全力投入開幕展,團隊是按這個目標所組織,未來肯定是要有細項發展。我很清楚專家團隊是博物館的靈魂,我們有九個展廳,這次開幕盛宴端出了九盤菜,展覽成果是立竿見影,參展人數破表便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說非常成功。

博物館開幕與文宣
CANS藝術新聞:據悉香港故宮網路預約至少排到二個月後,這或許是當初團隊沒有料想的?
焦天龍博士:的確,這讓我大吃一驚,而且年輕人參與的多,我原來還有些擔心這個時候開幕會受到疫情影響會沒有人潮。為維護參觀品質,我們有限定參觀人數,每日約6000-7000人次。從來沒想到博物館竟然還出現了黃牛票,還是在疫情期間,為此我們還特別做了相應措施。香港有這麼多博物館都是免費參觀,香港故宮的門票要收50港元還一票難求,特展展廳更是熱門。對於這點我還是挺感動,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西化程度較高,但是香港大眾對中華文化仍是非常景仰喜愛。香港當然也有很多高水平的藝術館,但像香港故宮這種標誌性的博物館入駐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推動、傳承是很有幫助。
無論是在中國與西方,博物館展覽中國藝術的目的都是在推廣大眾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這是我們的專業。不分國度地域,國際大都會也好,香港也好,臺北也是,都是展示中華文化。香港故宮的設計符合當代對於藝術品的呈現與教育,在香港有這樣一個專業現代化的硬體,能讓我們從這裡開始來推動。

CANS藝術新聞:香港故宮開幕的確是造成文博界的轟動,第一步已經有人潮了,有了羣眾基礎,也超過您的預期,未來你怎麼看這個博物館?您是展覽的火車頭,您的願景是甚麼?現在僅有香港本地觀眾參觀人數都幾近滿載,未來博物館的館址還有可能擴建嗎?
焦天龍博士:香港故宮的開局是比較好的,在疫情期間文博界一片蕭條下我們逆勢出發,這個起步是很棒的。從長遠角度來說,博物館一定要向世界一流博物館方向來發展。世界一流博物館是要打拼出來的,不是自己說出來的,是要讓別人認同你世界一流博物館。
無論是館藏的充實,展覽的策畫,學術研究,工程項目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來發展。新冠期間讓香港閉關的時候我們有時間來逐步發展。可以試想一下未來香港開放後,我們會更加熱鬧。現在的觀眾僅限於香港本地民眾,不僅是國外觀眾還沒進來,連大灣區的民眾都還沒有進來,屆時來參觀的群眾是不可限量的。館址的擴建可以看情況,作為博物館的從業人員當然希望能夠再擴建,但那是第二步,是未來的事情了。

CANS藝術新聞:近期本刊製作的「後浪」專輯,其中有對年輕博物館研究員的系列採訪,您怎麼看博物館研究員的年輕化後,對博物館的策展、學術研究,文宣各方向影響?
焦天龍博士:博物館研究員的年輕化是整體的趨勢,博物館運用現在的社羣媒體也是與時俱進,緊隨時代的腳步。香港故宮就用使用像是 IG,Facebook等的社羣媒體,也製作了動畫,與觀眾有互動的聲光軟件,像是「走進明代的畫裡」等等,用各種多媒體的方式各種演繹展覽。但是我有一個主張,就不能過度,不能譁眾取寵。這些都只是吸引觀眾的興趣,對作品深入淺出的解釋。但是過度了觀眾就可能不能聚焦於原作。最重要的還是盡可能讓觀眾能用更多時間來欣賞原作,這才是博物館展覽的功能,不是來看動畫片的。這個演繹是輔助性吸引觀眾,那些技術增加作品趣味的一個加強效果,以一種現在觀眾能接受的方式,讓觀眾在短的時間內,能理解更多的展覽思路,還有研究成果。
拜目前網路社群媒體的發達,香港故宮開幕與各個展覽、展品在網上造成很大的迴響,甚至有熱情觀眾,自己做研究拍照片,圖文並茂的替我們做了「每日一物」,好多展品都成了明星了。透過媒體的廣大的群眾基礎,像是〈新華社〉也為了開幕展作報導,這次展出【國之瑰寶 — 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中的《洛神賦》的網路流量瞬間流量就衝到100多萬人次,這是傳統展覽很難做到的。讓全世界更多的人,透過不同的媒介如臨現場,按鍵就能看到從前讀書時教科書級的重要藝術品,這也是時代的力量。之前也說了,我們博物館現在一天至多只能接待5000人、7000人,而且每天都滿。
CANS藝術新聞:香港故宮有自己的館藏與館藏經費嗎?這幾年有些博物館像是大都會博物館都陸續將館藏拿到拍賣場拍賣,也是籌措運營經費嗎?
焦天龍博士:香港故宮創建以來已經有1000多件收藏,全都是來自香港收藏家們的捐贈。眾所周知,香港收藏家的收藏實力享譽國際,他們的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都展覽過。香港收藏家們都非常支持香港故宮,目前接受的捐贈,都是來自幾位全球知名的香港收藏家的重要收藏,像是「夢蝶軒」。「夢蝶軒」所捐贈的946件金銀器,已經讓香港故宮在全球同類的收藏名列前茅列了!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其他藏家的捐贈。未來香港故宮會慢慢的增加自己的藏品,這些藏品都會按照館方的計劃展出。像是「夢蝶軒」捐贈的這批古代金銀器,我們將在明年舉辦專題展覽。
香港故宮有一個獨特國外特色,就是採董事會。歐洲是另外一個系統,美國除了華盛頓外,大部分博物館都是由董事會管理,美國最好的博物館、大學都是私人的。政府補助有很多規定,也會要按照行業的要求,所以跟政府還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像我曾就職的丹佛美術博物館,是科羅拉多州最大的博物館,雖然跟政府毫無關係,但州長市長都是會關照。私人博物館館長不是由政府派任,他們可以自由獨立運作,如政府給錢當然好,但基本上不靠政府,所以館長、部門負責人除了專業外,募款能力很重要,他們必須有能力籌措博物館運作的經費。
CANS藝術新聞:據我所知有很多香港收藏家想將藏品捐贈給香港故宮,香港故宮需要哪方面的捐贈?審核的標準又是什麼?
焦天龍博士:我們當然是希望擁有最好的精品,我本人在各大博物館工作見過無數珍品,並了解藝術品的歷史定位與價值。從理想的角度來講,藝術品本身必須要能反映中國文化和藝術發展,但是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所以只要是我們認為符合博物館的標準,同時又是我館所欠缺。當然目前香港故宮剛成立,館藏上還是一張白紙,各品項的藝術品都能接受。然後來源清楚,藏家願意無償捐贈,我們有一個審核程序,經過審核委員會董事會一同審核,同意就接受。
香港藏家的實力是國際知名,這麼多年來我與大家都是好朋友。他們對許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館都有貢獻,像是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博物館有何鴻卿爵士與徐展堂先生的捐贈。收藏家是有分不同的類型,有的人我稱之為真正的收藏家,他們在收藏成長過程中雖然有進有出,但是他們出自真心的熱愛,在學習中了解歷史文化。尤其是老一輩的收藏家,完全出自於對文化遺產的熱愛學習去收藏。這裏面有種熱情,是與投資型收藏家不同的,他們也很願意分享給大眾,所以他們對捐贈很積極。在他們的收藏觀念裡認為藝術品千百年流傳下來,因緣際會到他這兒,在歷史的洪流裡也只是過眼煙雲,所以就有胡惠春先生「暫得樓」這種堂號。他們收藏的目的不是為了賺藝術投資的錢,買賣調整是有彈性的,這就與博物館有許多共同之處,最終目的也相同。尤其是西方的博物館,是有進有出,一切調整都是為了精進館藏。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生很多共鳴。
再加上香港收藏家都很熱愛香港,對於香港這塊土地都非常自豪。多年以來,就盼望著香港能有一個世界一流博物館出現,無論硬件還是軟件上都要與這顆東方之珠能夠匹配。所以當我們需要幫助時,他們的投入是很令人挺感動。我曾到「敏求精舍」做過幾場演講,他們很積極參與香港故宮。當然每個人能力不同、想法不一樣,有些收藏家之前還在觀望,他不見得相信香港故宮能夠做出啥來,但當我們做出來了,他們就可以放心進行下一步。雖然還有許多投資型的收藏家,我想這應該與博物館沒有甚麼關係。相信在未來,在收藏家支持下,香港故宮能逐漸建立起世界頂級的館藏。
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博物館,像是美國博物館的成長之路,要靠收藏家捐贈。大都會博物館也好,丹佛博物館也好,它在一兩百年的成長過程中,有無數的收藏家參與了館藏的建構。像是丹佛博物館歷年捐贈人數有400多位,多則捐贈1000多件,少則捐贈1件。所以我們未來也是如此,與收藏家保持良好的關係,慢慢的積攢家底。
博物館與收藏界的聯繫,全靠館長與專家,像是上海博物館在馬承源館長不斷的海外奔走斡旋努力,收藏家們共襄盛舉捐錢捐文物,上博如今才有這個規模;香港藝術館的司徒元傑館長,建構了吳冠中先生的館藏規模,他們的個人魅力,與收藏家良好的關係與彼此間長期交往的信任,對博物館有著極大貢獻。